1. α-对偶子是宇宙演化的遗传密码
2016年物理诺贝尔奖颁给对量子霍尔电导率随磁场变化的阶梯现象做出拓朴学诠释的物理学家 [1] ,这是近年来凝态物理的一个重要事件,或许标志着凝态物理从Landau典范(paradigm)转向拓朴典范的进程已被启动。其中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即量子霍尔电导的台阶高度都是精细构造常数α,而量子论的全领域中α也是无所不在 [2] ,这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量子场论的探究领域是高维、高能、极高温的宇观及微观层次,而霍尔电导的量子化阶梯则是低维、低温、强磁场之低能态量子的介观普适现象,此两领域差异极大,但为何α能把两者联系起来,且这种联系是否与部分量子场论的理论模型适用于凝态基本粒子直接相关,两者又与宏观层次的量子生物学有何联系。对于以上问题的探究结果,摘要如表1所示,依序说明如下。
2. 从量子真空信息场中涌现的最小作用量子
作为宇宙及其演化阶梯之第一平台的本原,最小作用量子h (Planck常数)或宇宙超常数
,在很多方面规范着由它所衍生的所有基本粒子。此包含表1所示之α演化阶梯各平台的本原量子。本原(Gk. Arche)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语境里,不但意指本体(ontology),同时指演化和生成;而物理(Gk. phusis)的原初意涵正是【存在之生成及演化的自然本性和本质】 [3] ,这些原初意涵在本文中被保留。
h或
做为广义相空间的极限物理量(相空间的最小面积单元),提供一个物理空间的基本极限,从而与涉及无穷的任何数学空间做出本质的区分。表1中的其他宇宙超常数(universal super-constant),如最短物质波波长的光量子、最小长度量子、最短时间量子 [4] ,以及最小广义磁单极子、α-对偶子、氢原子1s电子、以及DNA中的最小信息量子等,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纯数学的所有无穷做出区分。
最小作用量子
为测不准原理立下物理规范,即
,且
与
都不能无限小或无限大(其中Q表广义坐标或四元时空,P为其对应的广义动量,两者有对偶或共轭关系);它也为所有类型的量子化原理立下物理守则,即以
(其中
与
分别是Q与P空间的量子数)和Weyl-Wigner转换 [5] [6] 为主的量子化主流,减轻对重整化技巧的依赖。简言之,广义相空间是所有基本粒子表征其特性及行为的物理(非数学)空间。
另外,不管最先从量子真空信息海洋中涌动而出的基本粒子是甚么,理论上都可称之为最小作用量子。因为h同时也是所有基本粒子之内禀自旋的基元,Bosons有整数h的自旋,Fermions有半整数h的自旋。但这并不表示
可再细分,而是
可被共同分有,例如精细构造常数
可视为

Table 1. The Alpha-Helical Scale Law of cosmic evolution
表1. 宇宙演化阶梯的α标度律
是两个电子共同分有一个最小作用量子并与光量子交互作用,或一个电荷(e)与一个Dirac磁荷(
)(磁单极)组成一个复合准粒子(quasi-particle) (参下Dirac磁单极的量子化定则)。本文把这种复合准粒子称为 -对偶子,这一方面是电荷与磁荷有对偶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最小作用量子是广义相空间的最小面积单元,而Q和P之间的对偶性是物理学的根本(续参Dirac磁单极的量子化定则)。至于
中的2π是最小作用量子h在其背景场(拓朴场的拓朴时空)中的路径积分所获得的几何相位(或Berry phase),不是h所原有,它涉及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宇宙超常数 [4] 。
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有其特有的相空间(参下双重时空)来表征自身的存在和演化。只有在这样的对偶空间中基本粒子才能真正的持续显现自身,单独或分立的Q空间或P空间都只能看到基本粒子的部分面向,无法整体的掌握它们的生成和演化功能。这是最小作用量子持续衍生其他基本粒子的作用空间,表1中各演化平台的本原量子在衍生其家族成员时也是如此。这个最小作用量子和广义相空间涉及物理学的全领域不只是量子论的全领域。
至于为何两个相互排斥的电子能组成一个稳定的复合准粒子?这是因为任何基本粒子都有自旋,而自旋普遍具有极性(polarity),例如手征性(chirality)、左右旋性(helicity)、顺反涡性(vorticity)等,根据费因曼路径积分的说法 [7] ,极性相反的两个费米子可经由路径积分的建设性相干而结合成玻色子(这是超对称的一种最简单解释),此与超导体中两个自旋取向相反的电子共享一个声子形成古柏对(cooper pair)的情形相同。
3. 基本粒子的物质波波长和Compton波长
任何基本粒子的描述都需要双重时空,一是外加的钟表时间与坐标空间(简称【机械时空】),另一是由其特性波长和周期所决定的量子时空 [8] (或可相对的称之为自然哲学的【生命时空】或拓朴量子场论的【拓朴时空】)。而基本粒子的特性波长又可分为两种,一是自身的物质波波长
,另一是与光量子交互作用的的Compton波长
。但有两个例外,一是光量子或其他无质量的基本粒子(如Weyl费米子)只有
没有
,此可由
的定义即可看出。另一是最小作用量子,它不遵守Q或P表征之波动方程的规范,所以没有
和
。但它拥有在相空间中表征自身的特有量子态,称为准机率分布(quasi-probability distribution),这种量子态的运算规则与波函数不同 [5] [6] [9] [10] 。
由表1知,从最小作用量子到DNA,不同α之幂次平台的本原量子,它们作为衍生相应平台之其他家族成员的本原,其物质波波长和Compton波长都具有相互嵌套、逐级升降的情形,本文把此现象称为 的螺旋标度律,并以此来划分宇宙演化的各个阶段,这是揭露Feynman所称α世纪之谜的首次尝试 [20] 。
以氢原子1 s电子这个宇宙演化阶梯的第四平台为例。氢原子是周期表中质量最轻的原子,其1 s电子又是能量最低的量子态。物理学中虽然大量采用数学,理论物理的数学主义者甚至坚信【数学的实在等同物理实在】,但物理和数学事实上存在一个本质的分野,那就是物理只能探究有限,本质上不能涉及无穷(如前述)。只能以有限的大小作为基元、作为本原,它们不能是无限大或无限小。氢原子1 s电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而成为原分子世界的本原,且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和有效积累,如何由这个原初始基衍生出原分子世界之森罗万象的过程与机理,相对而言,比其他平台都理解的更加丰富且详实,可做为其他演化平台建构理论的参照。本文以下仅就尚未被探究之最小α-对偶子(第三平台的本原)以及DNA之最小信息量子(第五平台的本原)的衍生过程,在现有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初步探索。
4. 量子霍尔效应的α-对偶子诠释
凝态二维电子气体系统中所显现的诸多量子霍尔电导率的量子化现象是当代凝态物理的最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尤其是以拓朴流型(manifold)的多元曲率和拓朴陈数等来解释这种量子化的根源,为凝态物理理论开启了一个以拓朴学为根基的全新视野。前述表征基本粒子之生命时空的广义相空间,正是一种具有深刻物理意涵之拓朴流型的参数空间。
4.1. 量子霍尔效应中的宇宙阶梯密码
量子霍尔效应(QHE)家族成员(诸如IQHE、FQHE、QSHE、QAHE、FQSHE、拓朴HE、skyrmion HE、能阱HE、复合准粒子HE等等)之所以获得特别的关注,不只是因为这些实验数据无法以旧有的Landau理论来解释、或引进了新的量子化机制、或开展了拓朴材料及拓朴相变的新领域、或突显了【物与几何(拓朴、形数)同一】的自然哲学指引等等,还在于它们都有极高的精确度和极强的普适性。无论材料的种类、形状的几何参数、杂质含量、甚至是传导量子的浓度,只要这些因素的量值不超过某个临界值,那么霍尔电导之量子化的阶梯印记都能精准地显现出来。它们似乎包藏着源自宇宙演化过程所内化的遗传密码(参下),而可作为凝态物理新拓朴典范的一个稳固的始基和生长点。图1a是单层石墨烯之量子霍尔电导率随磁场变化的阶梯图 [11] ,图中显示台阶高度是4α,依据前述α-对偶子整体传导的设想,此表示石墨烯单位晶格内有四个稳定的量子阱,足以局域化(localized) -对偶子,只有在磁场强度达到一定的量值时,它们才沿着Landau能阶的扩展态(extended states)在全局中传输(图1b)。
石墨烯是量子元器件的热门材料,也是量子计算器的潜在候选者,而其中的α-对偶子则是量子位(qubit)的原型。这种材料是否能发挥它所应有的上述功能,关键在于如何操控α-对偶子,以及能操控到甚么程度。另外,石墨烯和组成生命体的有机巨分子(含DNA)又有演化上的深层联系,因为所有的有机巨分子都以碳为骨架,且很多生命有机分子的碳骨架和石墨烯一样都是六边形(例如醣类、脂肪、DNA碱基及神经网络等)。做为表1所示之宇宙演化第四和第五阶层的中介,石墨烯在对偶空间(拓朴参数空间、广义相空间、也是量子位的Bloch球面和旋量空间)上的动态演化路径,是一个涉及宇宙演化的神秘(未知)过程,也是量子计算的设计和操作平台。
前述量子霍尔效应的拓朴诠释已经获奖,但这只是建构理论的开始,远远不是终结。以 -对偶子作

Figure 1. Graphene quantum Hall effect and Landau energy level [11]
图1. 石墨烯量子霍尔效应及Landau能阶示意图 [11]
为传导量子来解释这种量子化现象就是一种新诠释。这种新诠释的历史脉络至少可溯及Dirac的磁单极假说,由此所推衍的结论可与表1中所述之理论脉络相联系。
4.2. Dirac磁单极的量子化定则
1931年P.A.M.Dirac在其<<电磁场中的量子化异点>> [12] 一文中,尝试解释电荷量子化的物理成因,这是经典物理和当时的量子力学都无法解释的大问题。在经典物理中电荷是唯一量子化的物理量,量子力学建立后,任何物理量都可在算符化之后,作用在相应的量子态,求其特征值而量子化,但却无法从既有的有物理根源的量子化定则中,解释电荷量子化的成因。
Dirac发现,若假设磁单极
存在,则它在空间中所建立的位势是一种向量势(vector potential),此与电荷所建立的标量势不同,也是Maxwell原初方程中所无的一种新位势。在此向量势A的等位势球面上运动的电子将受到
之磁场的作用。其中
,是
、
两联立方程的解,但在磁单极所在的位置(r = 0处)
发散,是Dirac论文标题所称的电磁场中的量子化异点(Quantized singularities in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s)。当
(正z轴)和
(负z轴)时,
分别代表
的两极(N极及S极),后称Dirac弦极(Dirac string singularities)以与量子场论中的弦论相联系。
已知电磁场中的异点可经由规范转换(gauge transformation)来消除,在本例中此对应于
(上半球)与
(下半球)所对应的电子波函数
在赤道面(
)相匹配。即若
(gauge transformation),则对应的电子波数
。为了保证
为单值函数(即电子在同一处不能有两个不同机率密度),
只能为1,此表示
,其中n = 整数。因为
,代入上式得
(1)
这就是著名的Dirac量子化定则。
后来的研究显示式(1)包含巨大的信息量,例如:
1) 宇宙中只要存在一个磁单极则电荷必然量子化,这是电荷量子化的最原初成因,解决了上述电荷量子化的历史问题。
2) 由式(1)知
,其最小值(n = 1)为
。此表示最小磁单极所携带的电量为氢原子核(质子)的137倍,其对周围电子的吸引力也是质子的137倍,因此其1s电子轨道半径只有氢原子波尔半径
的1/137,也就是
,故最小α-对偶子(最小磁单极子与电子的复合粒子,有如氢原子是质子与电子的复合粒子)之1s电子的
。前述任何物理量都必须有限不能无穷,所以最小磁单极也应该有个最小值,已知最小长度量子lu是长度的极限,也是宇宙超常数,所以磁单极不能小于lu,而lu又正好是0.0243A的α倍(表1)。
3) 任一基本粒子只要带有电荷,它潜在的就能与一个磁单极(或磁通量子)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准粒子(例如Dirac Composite Fermion or Boson),只要条件适合这个复合准粒子就会显现出来。在上述量子霍尔效应的实验中,这个从潜在到显在的条件已经明确,就是低维度(2D以下)、深低温、强磁场的低能态。这个复合准粒子尚未被命名,本文称之为α-对偶子,原因如前述。这是对量子霍尔效应的一种可能诠释,因为它直接解释了量子霍尔电导率的α阶梯效应,固亦可模拟原子能阶间跳渡的光量子,称之为α量子。
4) 式(1)不但适用于本例中的电磁场,也适用于弱场、强场、大统一场、以及量子真空场 [13] [14] [15] [16] ,这只要将量子电动力学的U(1)规范群嵌入到(embedded)一个更大的统一规范群中即可。在这些理论中,磁单极子表现为受拓朴保护的平滑非线性场的场量子(topological solitons拓朴孤子),且它的存在是大统一场论(GUTs)的必然。因此广义磁单极可以是【所有场量子的共有属性】,包括凝态的晶格场、拓朴场(Berry曲率)等。同理,α量子也可以是【所有带电基本粒子的共有属性】。
5) 式(1)突出的显示了【对偶性是物理学的一种原初本性】。它不但包含经典电磁学之电荷与磁荷、电流与磁流、电场与磁场的对偶性,也包含了量子场论中强场与弱场的对偶性,以及超对称中费米子与波色子同一的对偶性,甚至是任何量子位(qubit)的极性对偶性(例如手性(chirality)、旋性(helicity)、涡性(voticity)),以及描述基本粒子或量子位之Wigner函数(quasi-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5] [6] 所需的对偶相空间(表1第一平台的广义作用量空间)等。它不但适用于高能高维的弦论 [15] ,也适用于低能低维的凝态物理,这个事实或可解释为何TKNN的理论模型中 [1] ,把强磁场和弱磁场视为无法言说的对偶场,却能成功解释量子霍尔效应的原因。TKNN模型中的另两个不可言说的【准电子波函数的Z2对称性】,以及【填充因子只能是有理数】(源自Harper模型 [17] ),正是α-对偶子的本性。
6) 式(1)中的整数n与拓朴陈数(cheng number)在本质上相同。这个结论是1975年,T.T. Wu和C.N. Yang [18] 所提出的,他们发现若令式(1)中的
,则
,这是量子规范场之场方程的一组解,具有Abelian规范群U(1)转换不变性。所以Dirac的磁单极可被视为是Abelian规范场的一种场量子。
综合以上结果得知,上述的广义Dirac量子化定则确实是一种更深刻的新量子化定则,不但不同于数学传统的特征值问题和最新的拓朴量子化(陈数),也不同于哥本哈根传统的广义坐标空间的量子化定则,它或可称为【参数空间之路径积分的量子化定则】。在此之参数空间包括Dirac的位势空间(动量空间),也包含拓朴流形空间(manifold),以及任何数学空间或有明确物理意义的任何物理空间,例如描述量子位的Bloch空间、旋量(spinor)空间以及本文所特别强调的广义相(作用量)空间(表1第一平台)。
5. DNA的X射线谱及其量子信息元
把 螺旋标度律从原分子层次(表1第四平台)再往下一个层级(表1第五平台)就进入到有机巨分子的世界,这就与DNA的组成成分相联系。若DNA中确实存在本文所称的量子信息元(信息量子),那么它的最小物质波波长将是氢原子1 s电子物质波波长的137倍(约455.3606A),其角波长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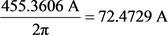 ,Compton波长将是3.3238A。由图2(c) B型DNA的分子结构得知,双股螺旋中的阶梯间距精确值是3.38 A [19] (间距平均值3.33±0.13A,预测值是
,Compton波长将是3.3238A。由图2(c) B型DNA的分子结构得知,双股螺旋中的阶梯间距精确值是3.38 A [19] (间距平均值3.33±0.13A,预测值是 ),而双股螺旋两周期的长度(图2(a)中所示的C周期)也确实是
),而双股螺旋两周期的长度(图2(a)中所示的C周期)也确实是 (预测值是72.4729A)。
(预测值是72.4729A)。
图2(a)与图2(b)互为对偶空间,DNA双螺旋的回旋周期是4π而非2π的事实可由图2(b)的最小间距是1/C而非1/P得到左证。所以图2(b)既是DNA局域分子的X射线谱,也是本文所称DNA中之最小量子信息元(信息量子)的能带结构图。它和图1(b)石墨烯的能带结构有很多相似处,不但上下两能锥在中心处相互接触(Dirac圆锥),且每个能带都呈现量子化现象(Landau能阶),这些量子化能阶直接解释了石墨烯量子霍尔效应的α阶梯图1(a)。至于在深低温强磁场的条件下DNA是否也会呈现出量子霍尔效应的α阶梯图则尚属未知。
综合而言,因为DNA缺乏量子层次的精确数据,所以还无法藉助实验来精炼理论,但若接受现有的实验数据则其与理论预测值的误差也只在1%~2%之间(甚至更小),因此可审慎乐观的称DNA中确实存在最小量子信息元,且既然其波长和周期为已知,则其本质已被掌握,可据此建构相应的波动方程来进行理论推演。
然而为何DNA之最小量子信息元的周期是4π,而不是一般的2π。这是因为双螺旋之左右股的螺旋

Figure 2. DNA X-ray spectrum and its double helix structure.
图2. DNA X射线谱及双螺旋结构示意图
性相反,当两者缠绕成双股时其周期变成单股的两倍。而究其初因,是量子信息元之波函数(或Wigner函数)的几何相位(又称Berry phase)在完成一周期(2π)时只产生 的几何相位变化(这个意义上的π是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宇宙超常数;其余四者在表1中 [4] ),必须在完成两个周期(4π)后才会有2π的几何相位变化而完成双股螺旋的一周期。在拓朴学上周期为4π的波函数(或Wigner函数)被称为具有Z2对称性,而只有具有Z2对称性的基本粒子才有量子位(qubit)的功能。此与前述两个极性相反的费米子,当两者的路径积分产生建设性相干时,会结合成具有Z2对称性之玻色子(例如α对偶子)的情形 [7] ,在理论上完全等同。
最后,从演化论的视野来看,最小量子信息元(信息量子)的能谱、氢原子的能谱、以及石墨烯中α-对偶子的能谱同构(isomorphism),这可能不是巧合而是三者有演化上的联系(表1)。因为氢原子、碳原子和DNA都是宇宙演化的产物,α-对偶子的量子化阶梯和氢原子能谱是宇宙遗传密码的一部分,生物DNA中量子信息元(信息量子)的阶梯状能谱(2b)也是遗传密码的一部分。这些宇宙遗传密码同构的事实,显示它存在某种标度不变性(scale invariance),而这种标度不变性就是表1所示的宇宙演化的α螺旋标度律。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显示宇宙演化阶层的α螺旋标度律有很宽广的理论背景(涉及量子论的全领域)和极高精确度及普适性的实验(量子霍尔效应)支持,因此表1所示的结果,偶然巧合的机率很低。虽然任何理论都只是人为的建构,寄托着建构者的无限热情和幻象,但这或许是揭蔽之路上持续前行的必要动力。本文的主要意图是为量子时代所需的各种产业(如量子元器件、量子计算器、量子网络、量子神经工程、量子人工智能、量子虚拟现实和实境虚拟等)提供一个新理论图景,并以此为基础参与量子时代的宏伟征程。
6.1. α-对偶子是介观尺度量子位的原型
从本文的视野来看,作为宇宙演化第三平台之本原的α-对偶子是量子位的原型(prototype),不管它以甚么面目呈现。例如量子阱中的离子、原子、空位;或超导cooper pair、复合准粒子(Dirac Composite Fermion or Boson)、skyrmion、任意子(anyon)等等,都将涉及这个本原。问题只在于如何操控这些量子位间的量子纠缠及量子运算,以及能操控到甚么程度。不过目前的技术显示,操控这些量子位需在深低温、强磁场的严苛条件,这使得这类量子计算器既庞大又昂贵,所以纵使IBM和Google在2022年能兑现承诺,让它们所生产的量子计算器商用运转,但这离全民量子时代的想象似乎仍是相当遥远。克服这个困难的可能途径除了现有拓朴材料及操控技术的有效突破和创新之外(例如微腔激光共振衍生及激光驱动之人造超强磁场),另一可能选项是作为宇宙演化第五平台之本原的DNA量子信息元。
6.2. DNA中的量子信息元(信息量子)可能是传颂中的理想量子位
与α-对偶子相比,DNA是宇宙演化的后期产物,历经更严苛的天择淬炼,拥有更复杂的组织结构、更高等级的自我调控能力、以及众多在演化过程中内化且尚未被揭示的遗传密码,它们大都以冗余的方式储存在DNA中。
这些无可取代的特点使得它的量子信息元有可能在现有的环境下(即常温、常压、弱磁等)也能执行它的量子功能。如果这一奇迹在工程上实现了,那么只要在所筛选的DNA片段两侧安置多功能的石墨烯(如做为基底、组分、电极、电池、封装保护等功能),那么一个DNA混成石墨烯的量子FET就可完成,后续的集成、设计、制作所欲的QPU、读写光盘及周边配备等至少可模拟电子FET和电子计算器的既有经验来取得进展。不过这当然只是初步设想,量子元器件与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和设计理念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6.3. 量子生物学可提供创造和生成的一种必要自由度
到目前为止这条量子时代的DNA进路,除了本文所称的最小量子信息元之外,仍处于想象阶段。但藉助物理学对量子思想、方法和操控技艺的超百年积累,只要确认DNA中确实存在多尺度的量子信息元,那么量子物理学的丰富知识、经验和技能,将成为建构量子生物学的坚实基础,它将为分子生物学增添一个运动和操控自由度。根据拓朴学关于拓朴相变的一个普适原理,被围困的二度空间生物只要具有三度空间的意识,那么纵使它没有演化出飞行或跳跃的能力,也能经由既有的爬行能力脱离困境。把分子生物学(表1第四平台)提升到量子生物学(表1第三平台)就是那个经由创造和生成来脱离分子生物学和DNA量子计算器现有困境所必要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