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著作和电影作品,这两者都有着非比寻常的艺术魅力。自此上世纪电影艺术诞生以来,许多电影
导演将这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门类结合起来,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经典电影。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佳作非常多,如《乱世佳人》、《战争与和平》、《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哈姆雷特》、《日瓦戈医生》、《堂吉诃德》、《简爱》、《老人与海》、《雷雨》、《祝福》等,这其中的成功之道自然值得深入探寻。
简而言之,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门类的叠加,往往能对观众产生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文学是艺术之母,是剪裁的艺术这意味着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门类有其相通之处。将成功的文学著作改编成电影自然是电影艺术家获得成功的一条捷径,但也不乏平庸之作。那么文学著作改编电影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创作规律?我们先从二者的关联说起,逐步剖析文学著作影视化的现象。
2. 文学与影视的关联
如果抛开“影视”的传播媒介、技术手段,单纯从一种表演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电影与戏曲、舞蹈、歌剧、音乐剧、话剧一样,都是一种表演艺术。“演”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为了生动形象地阐述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脚本都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便注定了文学与影视是可交织在一起的艺术。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这是艺术与生活的基本关系。无论是从艺术的起源,还是从艺术创作的主体或者题材考量,我们都可以发现艺术与生活不可分割这一基本规律。回顾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这个伟大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当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艺术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精神成果如诗歌、舞蹈、绘画等又得到广泛传播。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在一方面限制了文学著作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表演艺术进一步的昌盛。普罗大众不一定都能识文断字,但一定能看得懂表演。由此,各个阶级的民众都可以从表演中直接汲取精神文化的养分。以戏曲为例,戏曲文学是戏曲艺术的基础,离开戏曲文学,谈戏曲的发生、起源与形成,就会缺乏实际意义。
这样看来,似乎是文学奠基并促进了影视文艺的发展。然而,让我们大胆设想文字出现前人类的文艺生活。那些在篝火旁跳起来的舞蹈,无不表达着生活中的五颜六色:激烈的狩猎,安逸的农耕生活,丰收的喜悦,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些原始的表演以生活为脚本,并不依赖于文字媒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艺术也来源于生活,如根据911恐怖劫机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片《93号航班》、基于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事件拍摄的电影《女王》、以数学家纳什传记为蓝本的影片《美丽心灵》,以及根据1912年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拍摄的《泰坦尼克号》等等,这一系列优秀影片都以生活为蓝本拍摄而成。
这些电影作品都取材于生活,而且文学著作和电影甚至可以互为素材——既有根据成功的影视作品改编而成的小说,也有根据文学著作改编的影视作品。现今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暮光之城》,便是由于电影大获成功,而应市场需求改编出版的同名小说。而由文学著作改编的电影,更是不可胜数。由此可见,文学和影视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文学是生活及思想的提炼,影视文艺可以直接取材生活,亦可由文学作为基础改编而成。
3. 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必然
不过,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文学著作影视化,而影视作品文学化则相对较少,这中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以我国为例,文学的平民化和普及是上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民众主要通过各种戏曲、戏剧等舞台艺术来间接接触各类文学著作。而且读者对文学著作的理解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尤其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然而影视文艺作品则没有那么多的界限,也不受文化程度的制约,因此更受大众青睐[1]。文字是沉寂的,影视是鲜活的,沉寂的文字藉由鲜活的影视展现在大众面前,也达到了一种文化传播的效果。
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变快,影视作品创作成为一种商业化、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原创经典作品难以出现。人的心境也变得浮躁,图快捷、贪便利,这一方面影响着剧作者,使好的剧本千金难求。另一方面,受影视作品生产商业化、市场化的影响,影视剧本大多按照市场和投资方的需求,这也决定了好的影视剧本难以面世。
这样一来,“炒陈饭”就成了一个捷径。文学著作本来就是一本极好的影视脚本,既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有社会影响力,很早就得到了读者的推崇。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很容易有好的市场效益,可谓得名又得利。因此,文学著作影视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4. 中外文学著作影视化的代表作品
中外文学著作的影视化有些颇具代表性。观照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我们可以发现经典文学名著几乎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如《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飘》、《简爱》、《安娜卡列琳娜》、《茶花女》等。例如,根据玛格丽特的巨作《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即是文学著作影视化的成功典范,盖博和费雯丽精湛的演技,将故事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观众多年后仍然回味无穷。好莱坞成功的例子还有根据小说《教父》改编的同名电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龙•白兰度的通力合作,使得这部影片忠于原著而且精彩非凡。
根据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也不乏佳作。1990年底,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展奖项。由张艺谋执导的另一部电影《红高粱》,则改编自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这部电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许多优秀的文学著作被搬上荧幕,受到广泛好评,这其中编剧功不可没。
5. 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原则
有人说,“文学能够(而且首先能够)为真正的银幕创作提供丰富多样的题材和形式:神话和传奇、主题、情境、题材、风格、美学观念,尤其是语言风格、人物心理和读者心理等方面的宝贵经验。”[2]然而文学著作影视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遵循一些原则,使得不改变原著中心思想,又能转换成影视语言,具备影视文艺的特点。
首先,改编时不仅必须尽量避免、删除、转化原作中那些不能通过视听手段加以有效表达的内容,还需把原作的内容转为视听形象。也就是说,通过改编原著所拍摄出来的影片要能看,要有一定的画面感。常用的方法有:1) 细化情节,增加细节。由于细节是生动的、真实的,当在细节上进行加工拍摄后,也就增加了影片的可视性。2) 尽量运用镜头语言,让小说中的文字描写变成可看、可听的画面。
以由鲁迅小说《祝福》[3]改编的电影《祝福》为例。祥林嫂深入人心的形象刻画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可原著开篇出现的并不是祥林嫂,而是以鲁家的一个亲戚——“我”作为引子切入的,从北京回到家中过年,听人说祥林嫂死了,鲁四老爷非常反感,觉得大过年的喜庆日子还死了人,对祖宗也不吉利。由此,使“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听见过的印象中的祥林嫂以及祥林嫂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回忆来讲述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最后又回到鲁家过年的喜庆场面。如果严格按照原著来拍摄电影的话,剧情中就要出现“我”这个人物形象,由于“我”仅是个事件的叙述者,只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出现,作用并不大,再在影片中出现就显得多余。于是影片《祝福》就将多余的“我”删掉,而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祥林嫂命运的展开,使得故事曲折,细节真实,影片也就成功了。
同时,电影《祝福》[4]也很好地运用了镜头语言。在写祥林嫂死的时候,原著小说中仅有一段,文字叙述大意是:在年夜的爆竹声中,祥林嫂歪歪斜斜地走着,终于她倒下了,雪纷纷扬扬地飘在她身上,把她埋没了。小说中仅此一笔,但在影片中,首先是一个全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紧接着通过三个特写——脸、棍子、空碗,再加上大雪纷飞的氛围,一下子就把祥林嫂当时的处境刻画得非常生动。接着运用自下而上的摇镜头,表现祥林嫂的一双破鞋、单薄的裤子、千疮百孔的衣服、苍老的面容满头白发(如图1(a)),最后将镜头拉开,让观众清楚地看到祥林嫂颤颤微微地走着(如图1(b))、摔倒,以至于最终无法爬起来(如图1(c))。此时,画面中纷纷扬扬地雪花飘落,将祥林嫂掩埋,转眼间,观众便看不到祥林嫂的身影,眼前只呈现出了一个雪堆。像这样综合运用镜头语言,如特写、近景、推拉、摇移,再加上凄凉的音乐,就把祥林嫂的死刻画得淋漓尽致。除了原著的出色描写,它的艺术表现力主要应归功于影视艺术手法的运用。
6. 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利弊
1) 关上一扇门,推开一户窗
文学著作是沉默的风。沉默的风在一个人心底汹涌,只是一个人的情绪。而如果让这阵风刮出力度,刮出严寒和湿热,让每个观众内心都澎湃起来,则是影视作品的长处。
电影《魔戒》和《哈利波特》等魔幻系列作品,每一部的面世,都在全世界范围的观众中间掀起了一阵热浪。藉由技术手段,将冗长的文字描述乾坤大挪移一般,变成了让人叹为观止的魔法、世外之地。影片创造的虚构世界并非是和现实世界的影子,而是人类心灵的镜子,而这曾经是儿童的专利。再加上摄人心魄的音效,影片完全挥洒了书本中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人拍案叫绝。
这便是文字与影视的差异。前者直接影响读者的思想,而后者能把鲜活的东西直接送到读者的眼前。另一方面,影视语言也是国际化的,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渗透。
2) 多重解读与想象空间的消失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文学著作的理解是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然而导演只有一个,也就决定了影片是否能忠于原著,和导演是否能准确把握作者思想丝丝相扣。也要求导演保持中立,只作为照片的外延,把电影的多义性交由观众。现代影视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隐含着把意见强加于观众的危险,电影往往强迫观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取消了艺术的多义性本质,导演成了指挥观众的向导。
3) 直接和间接影响:文学与影视作品在接受上的差异
影视文艺可以直接把鲜活的影像送到观众眼前,而阅读一部文学著作则是细嚼慢咽的过程。二者间文化营养的供给和吸收过程有明显的区别。以波德莱尔在《把穷人打昏吧》(选自图2一书)中得这样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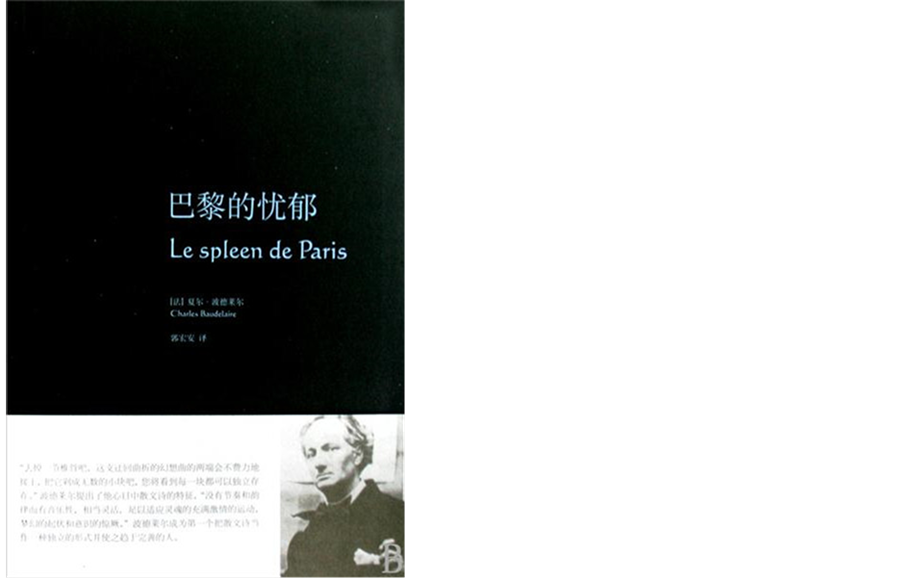
Figure 2. “Le Spleen de Paris” Baudelaire, C.P. 1869
图2. 《巴黎的忧郁》夏尔•波德莱尔1869年著
为例:“我走进一家酒馆,一个乞丐把帽子伸了过来,那目光无法忘怀。如果精神真能搅动物质,如果施行者的眼神能使葡萄成熟的话,那么这目光能使王冠落地”[5]。这样一段铿锵的文字是任何演员和镜头都无法表现出来的,也许将这段文字改编为影视语言只是一个3秒种的镜头,但这个镜头很难表现这样的一种力度。
由此可见,文学著作和影视作品各有其特殊性,可转化但不可替代。
7. 结束语
影视文艺本身既折射了当代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又反映了文化、思想和时代的变迁。在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当下,面对中国大量优秀的文学著作资源,新生代的导演不能急于求成,一味追求创作技巧,而应该沉下心来,积累丰富的文化基础和社会阅历,使自己的思想成熟起来,有能力体味到文学著作的多重含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思想和原作者的思想恰当地融入到影片中,得到观众的认同。随着影视创作的发展,必然会有更多的文学著作通过影视语言展现给观众。不过,作为观众的普罗大众也不能放弃对文学著作的阅读,只有对原著有一定的理解,在观影的同时才会取得更多的收获,文学著作影视化的社会意义才会得到更好的体现。